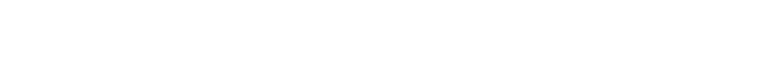刘鄂:行知精神的笃行者
数据更新:2022-05-04
“棋道一百,我只知七。”日本顶级棋手藤泽秀行对自身棋力的总结,一直提醒着我,面对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作为个体的研习者是何等渺小。当了二十年的法史学徒后,对于中国法律史,乃至主攻的清代法律史,我仍只是一知半解,前行之路任重道远。
——题记

“每施鞭扑心常恻,不事苞苴梦亦清。”作为施令者的杨炳堃在对于犯罪者实施刑罚时,常警醒自己心怀恻隐之心。所谓“苞苴”,本是指包裹鱼肉的草包,因为赠人礼物,必加包裹,所以馈赠的礼物也称为“苞苴”。再到后来,行贿的时候为掩人耳目,会对行贿物品加上包装,所以“苞苴”又代指了行贿的财物。杨炳堃说的“不事苞苴梦亦清”,就是说自己决不会为讨好上司而去行贿,这样自己做梦都是清爽的。
模糊生涩、隐喻却清醒的文字使得平面的楹联鲜活与清晰起来,跨越时间,徐徐走来。这一段对清代衙署楹联的解读,来自于金牌影院
教师刘鄂在央视《法律讲堂》栏目“楹联中的法文化”系列讲座中的主讲词。文字像弯弯曲曲的迷宫,文言文的晦涩难懂更是如此。为了将文字转为媒体化展示向大众普及学习,刘鄂耗费了很长时间,一做就是两年。
时间回溯到2019年,刘鄂在吉林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提交了一篇题为《以联为箴:清代衙署楹联中的法律文化》的学术论文。论文的选题角度和深度,得到了央视“法律讲堂”栏目主编孙辉刚先生的青睐,认为此论文可以向文化普及版的电视节目转化。二人畅谈,决心打磨。在双方深入沟通后,刘鄂与“法律讲堂”栏目展开合作,并最终站上节目讲台,以通俗易懂的话语,与全国观众分享传统楹联中的优秀法律文化。
在录制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让节目呈现出更好的效果,刘鄂一步一步明确写作方向、修改打磨脚本、纠正字词发音。“节目脚本的制作和学术论文的撰写方式有很大不同,我必须站在普通观众的视角去表达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以求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谈及上节目的初衷和准备过程,刘鄂说道。论文是以清代为背景的,他为了进一步延伸与完善这方面的内容,开始查证资料,将内容延续到民国时期。对于文章的打磨,他克服了许多困难。文字在不同时代所赋予的意义与符号的展示是不同的,尤其是包含时代意义的表述。除了对文字本身的含义进行不断推敲以外,刘鄂在文本讲述过程中的发音下了一番功夫。“你知道的,湖南人可能会因为一些口音的问题对于一些文字的发音并不准确。”为了尽可能使自己的发音更为准确,他找来了自己的学生,一遍遍地诵读,请学生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夜醒来,他还在琢磨“应”的声调。
针对这次央视播出节目在师生中引起的广泛赞誉,刘鄂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作品的打磨我已经重复多遍了,甚至形成了肌肉记忆,不假思索张口就能完整讲述。”刘鄂笑道。“去央视既是一个挑战,也是新的体验,我很喜欢去体验一些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学习起来很有意思。”
一、学习之度:时空与专业的跨越
和法制史的结缘并没有理想范式中的想当然热爱,怀揣着好奇和疑虑参半的心而接近,与时代洪流中的每一个个体普通又真实的选择别无二样,却也因为了解而热爱,因为热爱而坚持,因为坚持而明朗。出彩的不是选择的开始,而是志向的播种。
初入法史殿堂的门槛,刘鄂结识了一批相当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学习知识,钻研一个领域,不只是要读很多有意思的书,更重要的是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某个知识领域的有趣,是因为研究它的人、学习它的人有趣。某个知识领域的深度与广度,是由研究它的人决定的。”
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导师成为他心中遥不可及的高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是我那时对老师的感受,直至现在,这都是我所珍重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份敬重,促使刘鄂全身心扎根到法律史这个领域中去。
除了敬重的老师外,思想迥异、趣味完全不同的同学也冲击着他的想法,他为之惊叹并思索。“学习可以这么学,读书可以不局限于书上的东西,事情可以这般展开与理解。”他回忆到,“我们都知道法制史其实学起来比较枯燥,但对于我来说怎么去发掘其中的玩味,其实还是对一个知识的眼界和积累的问题,眼界决定你看这件事的广度,而积累则是对一门知识所挖掘的厚度。恩师与同学打开了我的视野,愈是接近,愈是多彩。”
志的过程或轰轰烈烈地结束,亦或历经考验、拨开云雾终有所得。前者与心绪有关,后者则需要恒久的积累,在积累中增加智慧,在智慧中重复积累。从博士阶段开始,除了完成大量的文献阅读外,刘鄂每年都会找时间去走访各个城市,“以前的旅游就是打卡一处风景,但是到博士阶段我开始探寻其他做学问的方式,不局限于纸张之上。我逐渐带着问题意识去走访每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很有目的性地去看古墓葬,去和不同的人交流想法、交换意见。真正对法史产生乐趣,其实就是我在读万卷书以外找到了行万里路的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格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的。
2017年的夏天,中缅边境的龙村,鸡犬之声相闻,刘鄂戴着草帽,在杂居的边境小村落来回兜转。为了深入了解田野的墓葬文化,他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龙村,“我之前做过相近的调查,但大多都是以墓见人、见习俗、见制度,而通过交流挖掘出丧葬文化信息,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不深入此处,便不能将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深一步思考。现实中,民众常将“太山石”当为“泰山石”,“这并不罕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及在佛教影响中国人的灵魂观之前,魂的去处之一即为圣山——泰山,故泰山为收魂之处。”行万里路是有它的意义的,刘鄂在解读历史留下来的痕迹,也揪住历史隐喻的尾巴追思曾经的风气与精神。“法律虽然是制定规则,但是最本质的目的仍然是对人,一定要呼应人心,这样才能直击心灵。如果对人的本身不了解,或者相对而言是比较窄的话,那么就做不到制定法律的初衷与目的——即回归到人的本身。为什么要走出去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因为对于一个问题的不同的人的认知和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在这里面你能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同了解与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你的眼界逐步就会被打开了。”
“做法制史研究的,其实是对风气的研究。何谓风气,摸不着、看不见,但它真实存在着。对于法律的研究,或者说是对人文文化的研究,其实是不可量化的。也正是不可量化的因素的存在,使得在这一行中的每一份积累都分外重要。”在研究古墓葬的过程中,刘鄂认识到对重视生命传承的中国人而言,为保护逝者的遗体、葬所而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生者明确生命的意义。“当听阿姨解释为什么要‘生基坟’,说到‘人要个家嘛’,我心里真是敲了一下。7月26号,我在龙村的另一个汉人组采访时,一位杨姓老者提到为何要好好砌坟墓时,也说到‘受了一辈子苦,死后要享点福’。”跳出课本,走出课堂,戴着草帽的刘鄂围着村庄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和农民无间地交谈着,细心挖掘着文化风气在每个人心中和身上吹起的波动和透激灵魂的涟漪。
今年正好是刘鄂学法史二十年的节点。“人生没有几个二十年,我的最青春的时光都在这里面度过了,到现在已经不能割舍了,已经完全沉浸到这个行当。”二十年前,少年骏马逐春风;二十年后,勤思内省,不坠青云之志。一颗初心的保留与坚守,是一名法学使徒谦卑的敬意与恒久的喜爱。用时间换成长,也用时间换一份清醒与明朗。
“我的学习之理想是这辈子能写一本在一百年后还有人读的书,就心满意足了。”他眼睛中闪着光。“这是我心中的一口‘气’,我想中国的文人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何写,能否顺利问世,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我很担心自己知识储备的匮乏,我想着这一切最后还是要问一问时间与阅历,很多东西只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着手去做。”对刘鄂而言,多元与趣味、广度与深度、知识与阅历是他不断自省与前行的深思;跨越时间,飞越地域,横越思想的局限,是他一直为之所努力的方向。
二、人生之态:主流中的非主流
消极与每个生命体长久共存。“我也遇到过那样的境地,整个人颓废停滞不前,感觉就是陷入了至暗时刻。”日夜颠倒,生活一塌糊涂,苦中何以作乐,但有时就是要跳出这个循环才能有所小成。“有时候处理问题,需要心理的鼓励和安慰,但更需要的是付诸行动去做事。在做事中不要追问太多为什么,多去问实际要做什么,用做什么来解决为什么。”刚刚参加工作时的他常忙到深夜才能到家,却不得不赶紧定下隔天曙光未至的三点的闹钟起来备课。“也正是这样,我对学生讲课才能更有底气,课堂所有的内容我会在脑海中反复思索数遍。”言语犹如启示,学生能够契合他所想传达的意向和精神。
法史的学习不是单一的解读和展示,它赋予了刘鄂一种“跨度”的能力,突破认识停留在对事物质的抽象而不是本质的抽象——即线性思维的弊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进行对话和解读,在解读和学习历史中获得与升华自己对思想古为今用的一种智慧。曾国藩的经历常使他清醒,“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也是如此”,这种别样式的阿Q精神却并非精神疗法的固执,更多的是和解后的奋起的一种超越。生性洒脱与乐观,重点永远不是前缀的“生性”,而是对苦难生活“越辩越明”的智慧、洒脱,不是一份原始,而是一种成长。
心至苦事至盛,智慧愈苦愈明。“这些年越来越注重每年都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其实也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心态,人生苦短,时间是线性向前的,谁也无法掌控。”力做主流中的非主流的他,怀揣着蓬勃的好奇心,在和自己对抗的基础上,与自己和解与撕裂,负重奔跑,依然在不断前行中。
“人生一世间,享上寿者,不过百岁;中寿者,亦不过七、八十岁,除老少二十年,而即此五六十年中,必读书二十载,出游二十载,著书二十载,方不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者也。”清人魏禧之言是他推崇的人生哲言,也是他生活的部分写照。
南方人物周刊写到: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世界里,接触着相似的事物,但不同的是,读书更多的人在感知生活的乐趣时,能够拥有更多的层次,更能体会表象之下所蕴藏的深刻趣味。刘鄂在读书,也在期望写书,他在读人,也在读自己,合上书,停住脚步,耕耘只为奉献。
三、授业之愧:法途漫漫,人师难为
二十多岁满心扎根积累,三十多岁奋力工作,如今迈过四十,时间和经历赋予了他更多的沉稳和思索。刘鄂始终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相应的,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视野和认知,新的一代一定会超越上一代人。他也在不断向年轻人学习,构建自己的多元思维,反对庸俗的、扁平的生活,在平静中发声,在温润中炽热,在同舟共济中活出自己的踽踽独立思索的洒脱。
“鄂哥,鄂哥”听到这个爱称,刘鄂略带腼腆地笑笑,“其实很不好意思,毕竟年龄差在那里,但我一直很尊重学生的表达,也一直在向学生学习,后来想想也欣然接受之。”藤泽秀行说过,棋道一百,我只知七。“很恐怖,他作为那个时代的最顶尖的棋手,说出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震撼发自内心,如果将法律的学习比作是一条线的化,对于他来说,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就如他的简介里写到:法途漫漫。多么简略却又不可一目见底的文字。“其实现在再遇到我读博之前所教授的学生,我是满心愧疚的,因为我总是在反思,那个时候我的知识储备是不足以能给他们更好的讲解知识。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我也一直不断在摸索。”为此,他秉持着讲课从来不重复使用课件的习惯,每次授课都是新的准备,也是不断进行着新的挑战。“这是我给自己的规定。”
相较法学老师和法学使徒,刘鄂道不出更偏爱哪一个角色,他认为这不需要有一个答案。他所做的,一直都是用虔诚的心挖掘新的知识,细心打磨与雕琢,双手奉献给自己的学生。“授课的功力高低不是别人评判的,其实内心是有尺度的。这一年读过多少书,有过多少思考,去过什么地方,经历过什么人,有什么交流,这些都将决定这一年的进步。进步对于我而言很重要,对于我的学生同样也是。”这是他作为法史学徒的动力,同样,也是作为法学教师的坚守。
“在教室里面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孩子学习法律,我自己也是法史的学徒,我们很像。”刘鄂借着教师的职业比喻这份工作,“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喜爱的专业,发现自己的特色,这很难得,我要努力。”
“对联所普及宣传以及本身所代表的含义在这时代不可避免的是被弱化了很多,但是透过对联的表象往深层次里,它就是一种宣传口号,再往深处讲,其实就是一种风气。我们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气,虽然承载的载体不一样,但是它的内涵,以官府的楹联为核心的清、慎、勤、恕这样的精神品质不会消亡,这种本质的内涵是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的。”当下的风气,有更多元的载体承载传播。当风气未定型的时候,它是有若干种可能性的,但是当它一旦成为一种套路的时候,就反而习以为常,可能没有更大的意义。刘鄂研究的清代有两千多个衙门门口都有楹联,“这个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贪官也会跟风如此,因此风气对人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对于内心赞同并为之努力的人,还是很重要的。”这些知识,唯有深入的研究才能作出浅出的表达,没有多年的功力,做不出这样的成果。“任何领域唯有满心扎根进去,摸索前行,经历自我认知的否定和超越,开始入门了,视野才能被打开,这需要慢慢用功。”他劝诫同学,读书求知时须更为耐心一些,以平淡的胸襟着力用功,才能看到更多东西。
“人生秀美奇崛的风光,往往在于险远之境,从平淡出发与努力,才能走向远方。”
谈及时刻挂念的同学,他顿了顿,平淡又炽热的瞳孔中闪着光,正如他细心阅读同学留言后认真书写的文字:“好些同学已多年未联系,他日纵使重逢,恐也一时难识。世事不定,过客匆匆,许是人生常态。只要双方人生交错时,彼此互存善意,这就足矣。相见亦无事,不见偶思君。送给每位与我有过师生之缘的同学。”
“他们会比我更好的,他们一定要比我更好。”